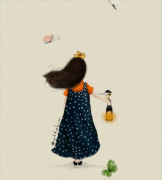| 摘要:老家有一块儿属于我的空地。 二十多年前在这块儿地上栽了些杨树,昔日的小树苗,栉风沐雨,已然长成了大树。树木成材本来该高兴才是,可它们快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 栽树苗的时…… |
老家有一块儿属于我的空地。
二十多年前在这块儿地上栽了些杨树,昔日的小树苗,栉风沐雨,已然长成了大树。树木成材本来该高兴才是,可它们快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
栽树苗的时候,四周围也都是空闲的宅基地。因为我们不常回老家,所以地基上就没盖房子,任杨树自由生长。后来邻居们陆续建起了住房,大杨树就成了祸患:树根拱了邻居的地,树枝扫坏了别人房上的瓦,落叶脏了胡同的地——告状的电话接二连三。除了道歉,剩下的只有一条路──刨树。我把心一横,刨树,一棵也不留,彻底解决后患。说干就干,妹妹帮忙请了专业的伐树队,两天的功夫,大杨树一棵也没有了。
树倒是没有了,可看着空院里杂草丛生,地势低洼,一到雨季,这里变成一个大水坑,实在影响村容。众亲友建议:拉土垫地。于是又一波工程启动。得亏是暑假,不然哪里有时间?当老师的优越性得以体现。
周一晚上,四辆后八轮大车把土送到胡同口,胡同口窄,不能顺利进去,只好把土卸在大街上。提前借的铲车一到位,忙碌的填土作业开始了。
开铲车的师傅中等个头,四十多岁,身体微微发福。第一眼觉得有点面熟,但始终想不起来他是谁。只见他熟练地驾车,铲土、倒车、转进胡同、填埋、后退、碾压……这些动作一气完成,车技是娴熟的很。两个小时的时间,土,全被铲进了院子。
休息的当口,借着月光,我们几个攀谈起来。铲车师傅点燃一根烟,吸了一口,看着我说:“老师,你不认识我了吗?我是你的学生,华齐呀。”我突然有所悟,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。
师范毕业,不到二十岁的我,被镇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从学区争抢到分配名额,要知道当时的中师生可是行业里的正规军。受过专业训练,到农村小学去,那可是学校里的香饽饽。普通话标准、业务能力强、基本功扎实。
八十年代的农村,改革开放不久,生产生活条件还不是很好。农村学校的面貌就更是不敢恭维。上班的第一天,一进学校大门,我就呆住了:刚下过大雨,校园里积水很深,我脱了鞋子,卷起裤腿儿,光脚趟水十几分钟才到了校长办公室。校长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简陋的大教室,除了办公桌椅,脸盆,再没有别的摆设。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,激励我困难是暂时的,努力工作,今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接着校长安排一位学姐领我熟悉校园。
校园里的每一个教室境况相同:窗户,几乎都没有玻璃,偶尔能看见塑料薄膜随风在窗棱上舞动。教室的门也很破,油漆剥落,门板少一块似乎很常见。校园两排教室之间竟然还有个鱼塘。
那时,我担任四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、语文、自然、品德,每周二十几节课。早上要出早操,晚上要看晚自习。为了工作方便,吃住在校。校长特意把学校里最好的一间宿舍留给我和学姐。那是一间怎样的房间呀:外面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;脸盆不光用来洗脸,还得用来接雨水。晚上躺在床上,透过屋顶的缝隙就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。
夏天还好凑合,一到冬天,我还得领着孩子们,自己动手把窗户用塑料布钉上防风雪,再和孩子们一起生大火炉子取暖用。我哪里会管理炉子呀,天天早起生火,第二天一看又灭了……
华齐就是那时候我的一个学生。他家是超生户,有两个姐姐,家庭条件因为华齐的降生,陷入窘境。父母忙于生计,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。多次的家访使我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,也给过他应有的帮助和鼓励。十年后,举全村的财力物力,一座可容纳十六个教学班的高楼拔地而起,校容校貌焕然一新,师生们欢天喜地乔迁新居。
华齐现在是一个运输队的老板,经营沙、石、水泥等建筑材料,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成熟的痕迹。他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:老师,我小时候调皮,没少惹你生气,可你总是鼓励我,男孩子小时候好好读书,长大了,才会有出息,才会有担当。岁月欠你的,时光都会补给你。
我说过的话,不记得了。但是华齐这个学生,我却记忆犹新。如果说他的成功,得益于老师的鼓励和教育。我倒是有一点欣慰。
告别老家众亲友回到县城,已是凌晨时分,初秋的风,有了几许凉意。月亮已经隐退,天上几颗星星疲乏地眨着眼睛,东边的天际已经发白。我毫无睡意,脑海中再一次浮现留下我十五年青春岁月的那个小学校。二十多年不见,记忆中的学校可好?还有那些不曾再见的孩子们,你们可好?抽时间我一定回去看看。

作者简介:
宋艳玲,获嘉县凯旋路小学数学教师。获嘉县第二届“感动同盟30年美丽教师”。
- «
● 编辑 : 娜娜 / 小威 / 沈晓沫
● 发布 : 娜娜 审核 : 朤朤 / 陌语
● 热线 : 158-1078-1908
● 邮箱: 770772751#qq.com (#改为@)